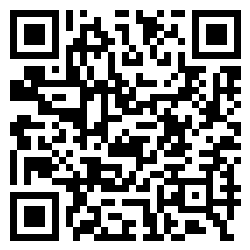黎族婦女自學(xué)技術(shù) 打造白沙首家有機(jī)綠茶園
清晨,被五指山和黎母山脈包圍的白沙盆地,云霧繚繞,38歲的黎族婦女符小芳帶著20位工人,手沾露珠,采摘嫩茶。這片茶園,不施農(nóng)藥化肥,是白沙黎族自治縣第一塊有機(jī)綠茶園,300畝地,已經(jīng)投產(chǎn)128畝,因距離著名的白沙隕石坑有5里路程,取名為“五里路”。
符小芳五指靈動,一片片翠綠的茶青,被摘下放入竹簍。“采摘的技巧很重要,一芽一葉(初長)、一芽兩葉和對夾葉,加工成的茶的品質(zhì)不同,采摘要分類。”符小芳說,在“五里路”茶園采茶,工人們需要背兩個簍子。盡管熟練,一人每天也僅能采6斤茶青。
茶園里的茶并不十分“艷麗”,田頭掛著滅蟲燈,依然有不少茶葉被害蟲侵蝕,導(dǎo)致產(chǎn)量不到正常茶園的一半。但是,符小芳堅持不使用任何的化學(xué)投入品,她說“這是底線”。
回憶起6年前,她向家人宣布種植有機(jī)茶的決定時,符小芳連自己都難以相信,她從沒有種茶的經(jīng)驗,更何況是種有機(jī)茶。“當(dāng)時,就是一種情懷”,符小芳出生于白沙黎族自治縣青松鄉(xiāng)牙闊村,黎族人世代嗜茶。“祖輩們都是上山采摘野茶,后來生活變好,開始購買茶葉”。
但是,規(guī)模化種植的茶葉,農(nóng)藥化肥的使用,影響了茶葉品質(zhì)和安全。符小芳說,最開始就是想能夠為鄉(xiāng)親們種出安全的茶,于是就在已經(jīng)被撂荒數(shù)年的田地上,種植有機(jī)茶葉。
但是,她從未想過種有機(jī)茶的投入如此之大,第一年每畝需投入1.5萬元,此后每年1.2萬元/畝。符小芳將自己的1萬多株橡膠轉(zhuǎn)讓出去,將所有的“家底”投到了300畝茶園。白沙職業(yè)學(xué)校農(nóng)學(xué)畢業(yè)的符小芳通過與老茶農(nóng)交流,很快就學(xué)會了種茶技術(shù)。
“還是交了很多‘學(xué)費(fèi)’。”符小芳說:“比如灌溉技術(shù),一開始我們像種橡膠一樣鋪設(shè)管道進(jìn)行滴灌,結(jié)果由于地不平、灌溉不均勻,茶樹長勢參差不齊。后來在專家的指導(dǎo)下,改用噴灌。損失了20萬元的滴灌設(shè)施。”
符小芳也曾有過放棄的念頭。2014年,白沙旱災(zāi),水庫干涸、河流變小溪,符小芳的茶園因干旱導(dǎo)致葉落,只剩下樹桿。更可怕的是,干旱導(dǎo)致茶樹“體弱”、抵抗力下降,病蟲害席卷而來。此時,她已經(jīng)拿到了中國有機(jī)認(rèn)證,正在申請歐盟有機(jī)認(rèn)證。看到日益蒸發(fā)的水分,符小芳想著用稻草來蓋下茶園,但是歐盟有機(jī)認(rèn)證機(jī)構(gòu)卻告訴她,如果這樣做就需要出示稻草的有機(jī)證明。
“當(dāng)時就不淡定了。”符小芳說。不過,看著茶園,看著工人,她覺得種有機(jī)茶不僅僅是“情懷”,也是“責(zé)任”。讓符小芳更為欣慰的是,丈夫王見君非常支持,甚至辭去了一家企業(yè)的廠長職務(wù),和她一起做有機(jī)茶、度難關(guān)。符小芳咬咬牙,沒有使用稻草覆蓋,挺了過去。
“我們也非常幸運(yùn),來自各地的專家們給了很多技術(shù)指導(dǎo)。比如,在茶園種上柱花草,就既可以提高土壤保持水肥的能力,柱花草也可以作為綠肥。”符小芳說。
在夫妻倆的苦心經(jīng)營下,“五里路”有機(jī)茶憑借品質(zhì)行走了萬里路,端上了聯(lián)合國官員的茶桌。“現(xiàn)在供不應(yīng)求,每斤茶葉賣到了600元以上,前兩天還有顧客以5000元一斤的價格買了數(shù)斤手工炒制的有機(jī)綠茶。”王見君說,有機(jī)綠茶投入大、前期艱辛,但是長久來看,可持續(xù)、能賺錢。
對于未來,符小芳有目標(biāo)、有暢想。但是,她輕輕地?fù)u了搖頭說道:“還不到時間,現(xiàn)在就是要靜下心來,一步一步地把產(chǎn)品做好做精致,不貪圖大、不貪圖來錢快。”
來源:海南日報
- 上一篇:種上“有機(jī)米”,減產(chǎn)反增收 [2016-07-16]
- 下一篇:沒有啦